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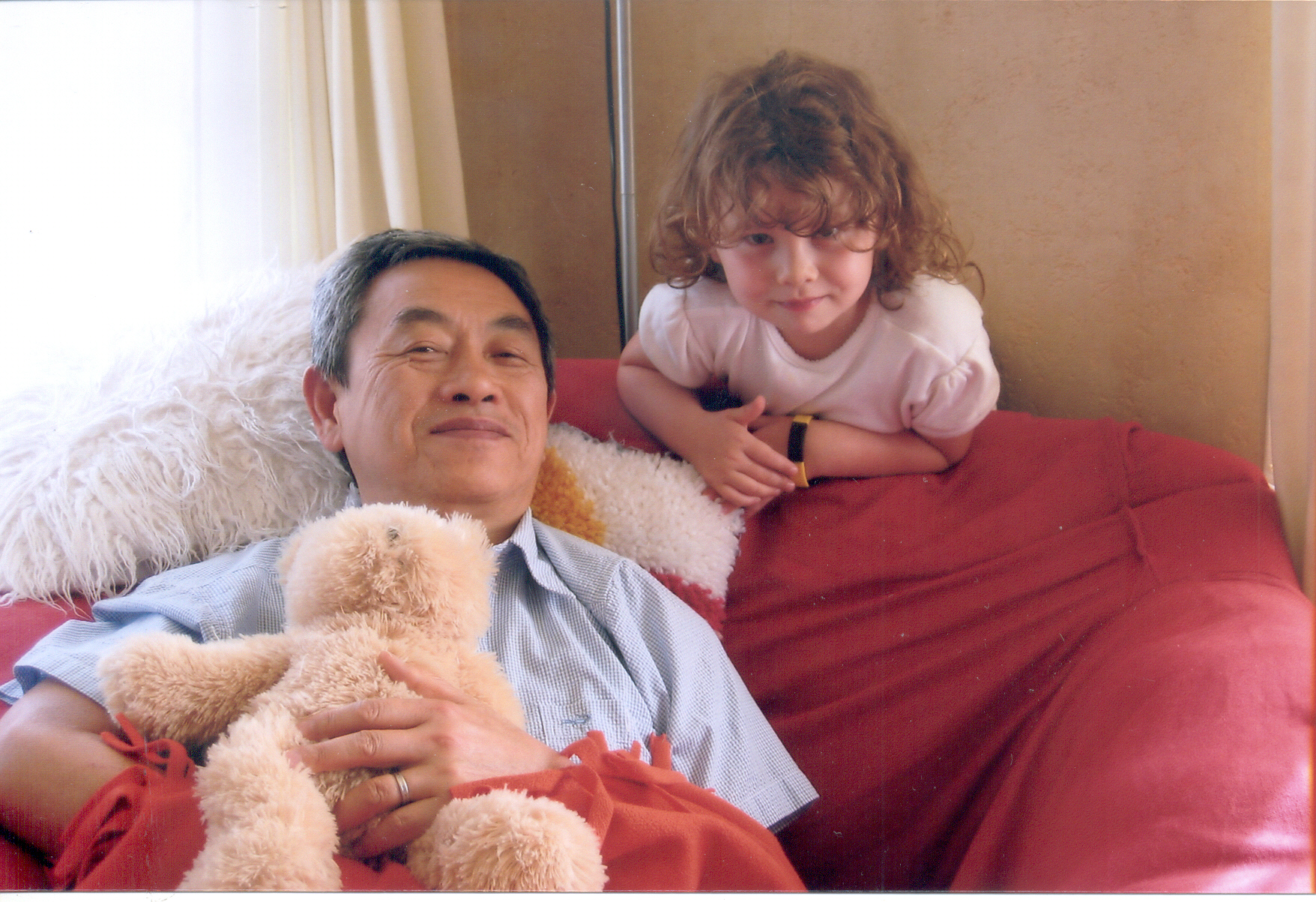

大地的出產,滋養和供應人們的生活需要,人在經歷種種困苦挑戰後重得喜樂、平安,向上主發出歡呼,作出感恩之祭,這是感恩節的源起。今日,我們生活在城市,人際關係常出現衝突和破裂,面對將來,我們可以拿甚麼來獻給上帝?
我在英國威爾斯牧會時,每年收割感恩節都會看到聖殿前擺着一個極大又漂亮的南瓜,是一位我從不認識的街坊,每年都特意在自己後花園栽種的,獻上的是他一年的感恩之心。但我們處身在這非農業的社會中,該獻上的是甚麼呢?九月底在倫敦循道會收割感恩節崇拜中,人們獻上的多是從超市購買的罐頭食品、乾糧和餅乾,在分享時提出為出產這些食物的國民所面對的艱苦貧乏處境禱告,更要去思考現今不公義的經濟貿易帶來的剝削和不公平,當我們盲目消耗這地球的資源時,對我們後代帶來的貧乏和苦難會是何等的大!
生活在一個戰火處處、難民有增無減、各國領袖為着個別利益、明爭暗鬥,甚至磨拳擦掌,彼此對敵,不單是國際間之權力鬥爭,也同樣出現在我們香港的社會中。近日的立法會宣誓風波更明顯地指出,我們怎能只着眼於個人的感恩!當週遭被強風暴雨、黑暗烏雲覆蓋時,我們要感恩的,是仍有一顆堅定不移的信心──上主與我們同在!
東正教會的巴多羅買教宗提醒我們要從大處着眼(see the larger picture),因為他看一切事物比他個人更重要,同時,他也是在信仰傳統中不能分割的一份子。就在這人心徬徨和憂患中,他提供了洞悉和盼望給這世界。
二00二年,他在奧斯陸接受了「智慧獎狀」,眾多獲獎理由之一,是讚揚他努力不懈地批評和譴責現今過度的消費主義,並因失去公義而產生的不公平制度。對他來說自我倒空(self-emptying)和犧牲(sacrifice)是信徒和教會可作的最好獻祭,更加重要的是信仰中的十字架和聖餐,是我們的福份和感謝之祭(without the cross, without sacrifice, there can be no blessing)。
如果在這感恩節中,我們經已籌到足夠的金錢去支付重建國際禮拜堂暨總議會大樓的建築費用,我們會很興奮;如果每個人私下禱告都得着應許,我們會喜出望外地謝天謝地。然而我更確定和相信的,是因着對上帝的信仰,我們可以忘記自己,效法基督,為他人和為這世界作出犧牲,讓這世界和社會的痛苦能減輕一點。
這是上帝今天賜予我們的恩典!
一九三三年世界戰雲密佈,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美國匹茲堡榭迪賽德長老教會(Shadyside Presbyterian Church)呼籲世界各地信眾每年於十月第一主日舉行普世聖餐主日,這建議於一九四0年獲美國基督教協進會正式通過及接納。
際此紀念二次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今日在聖壇前領受聖餐時,我們會有一種特別的感受──我們與普世教會合而為一,誠心誠意為世界和平而祝禱,求主憐憫,使人心得以改變,停止暴力行為,促進愛與和平,更要學效耶穌犧牲捨己的精神。
普世聖餐運動之發起及每年均獲得支持,乃因美國經濟大蕭條及二次大戰之遺禍,再加上當時歐洲納粹主義猖獗,人心惶恐,害怕更大的禍患隨之降臨。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在總統就職演說中的名言是:「我們唯一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可悲的是,我們並未從歷史汲取教訓。戰爭可以停止,冷戰可以結束,柏林圍牆可以倒下,金融危機可以消除,但自二次大戰結束後,我們只有短暫的和平,世界仍烽煙不斷。回顧過去,自一九七九年柏林圍牆倒下的短短三十多年,這個世人夢想的「新世界」仍然為着自身利益而壁壘分明、爾虞我詐、心思貪婪、豪取強奪,為求滿足一己之慾,妄顧弱勢社群,忘記了在自身以外,還有「普世」,只看到個人的利益、「我的」群體、「我的」教會、「我的」世界。
聖餐之所以為「聖」,乃因是「上主的餐」,是上帝的愛子耶穌基督以祂的死和捨己的生命換來的。我們不單單領受,更重要是得着耶穌的生命,學習祂的榜樣和教導。無論是信徒個人、教會群體或以基督教為國家信仰的國家,當信徒在敬虔領受聖餐之時,祈求上主潔淨我們,饒恕並赦免我們的自高自大和貪婪自私;更在這普世聖餐主日之時,心繫環球信徒,從日出之處到日落之地、從東至西,南至北,都同心在主前跪下禱告:願天國早日降臨!
V Day(Victory in Europe Day,歐戰勝利紀念日,歐美國家定於每年的五月八日紀念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德國在柏林正式簽訂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對信徒來說,聖餐便是我們的V Day,以信心紀念基督勝過死亡和黑暗權勢,和平仁愛終永存人間!
聖經,不單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書,也是使人「因在基督耶穌裏的信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15)。然而因各人對聖經的認知和領會各有不同,在實踐之時往往出現分歧和爭論,繼而產生了被視為「激進」或「保守」的教會,出現「開明」或「建制」等不同的名字。在英國,相對於政府體制之內的國教聖公會,循道公會由始至今仍是以自由教會為榮,不受政治勢力的牽制,有更大的空間回應社會民生、經濟,甚或是政制的處境問題。
香港在過去的三十年生活富裕,回歸後政治生態改變,教會日趨內向,而信徒也較喜歡追求歡樂、平穩的教會生活,漸漸遺忘了聖經的教訓是要學效耶穌基督的受苦生命——「為福音同受苦難」(提後一:8),甚至是「為義受苦」也是甘心樂意。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上帝的道,不單只是一本「使人歸正」、「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三:16-17)的書,更是「使人甦醒……使愚蒙人有智慧……使人眼目明亮。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詩十九:7-9)。我們閱讀聖經,重要的是體驗上帝的心意,從而得着能力,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國,與主同行,不斷創造一個更完善、公義、和平、仁愛的社會。
在不公不義、強權威嚇的社會中,要為貧困受苦的人伸張正義及為主發聲,確實不是大多數信眾可以做得到的。巴西大主教Helder Camara (1964-1985) 的名言是:「當我施捨食物給窮人時,他們稱我是聖人。當我問為何有窮人時,他們罵我是共產黨人。」「他們」都是在看同一本聖經的人,但當有牧者或教會要與貧苦的建制社會下的受害者同在時,便會受到質詢和批評,甚或是誹謗誣衊。
在改革宗中,聖經的權威(authority)是地上唯一的權威,我們要遵守上帝的聖言和命令。地上的政權也因上帝而來,律法固然要守,但上帝的典章律例更加要遵從和委身。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八日,馬丁路德在面對德國的帝王問他會否認錯,並收回所發表的意見時,馬丁路德說:「除非聖經或有理由清楚證明我是錯,我受所引用的聖經約束,我的良心受神的話捆綁。我不能,也不願收回任何的意見,因為違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當。我不能那樣作。這是我的立場,求上帝幫助我。」
聖經不只是今日,亦是昨日和將來的。有一天,上帝會再來,問我們是否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信徒,並有否忠於聖經的教訓。